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院长柴立元(前排中)及其团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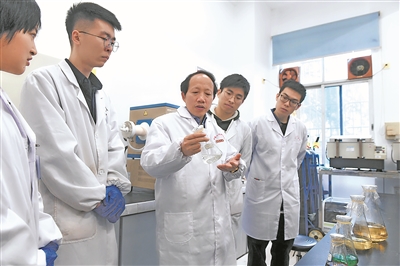
柴立元(中)指导学生做实验。
学的是冶金,但做的是冶金环境工程;岗位是大学教授,但许多时间是在矿山和车间;已功成名就成为院士,但“目前最操心的是技术推广,是技术与工程应用无缝对接”……中南大学教授柴立元,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学术人生中写下很多个“但”,唯一的原因是:以国家的重大需求为己任。
2013年11月,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他的实验室;2019年11月,53岁的他,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组建新学科:从一张白纸到全国知名
1985年,柴立元考入中南大学,当时学校还叫中南矿冶学院,“地(质)采(矿)选(矿)冶(金)”是学校的四大学科。10岁就没了父亲、家境贫寒的柴立元,来自江西偏远乡村的柴立元,以为学冶金就能淘到金的柴立元,懵里懵懂进了冶金系。
这一读就是12年,从本科到硕士、博士,再到做博士后,柴立元与冶金工程中的“稀贵金属的提取和精炼”,整整杠了12年。
以为这就是自己学术生涯的主攻方向,没想到,1999年,以优异成绩从日本访学归来的柴立元,受命组建具有冶金特色的环境工程学科。
环境工程?对读了12年冶金的柴立元来说,这完全是崭新的学科,而冶金环境工程,更是环境科学、环境工程和冶金工程的交叉学科。中南大学冶金工程学科在全国名列前茅,但加上“环境”两字,研究方向、研究团队、实验室建设……人财物全部是一张白纸。从何着手?能否不负厚望?柴立元感觉压力山大。
但是国家急需。我国是有色金属生产大国,2018年产值已过6万亿元。有色金属冶金生产过程往往伴随着废气、废水及固体废物污染。过去由于产量不大,环境问题还不太突出,改革开放后,我国有色金属工业飞速发展,污染问题日渐凸显。记者查到一组权威数据:2018年有色金属行业产生一般固体废物4.8亿吨,约占全国工业一般固废产生量的14.7%,产生危险固废721万吨,占全国危废产生量10%以上。组建冶金环境工程学科,刻不容缓。
加上自己才3个人,这个专业怎么建?读了一肚子书的柴立元,这个时候心里特别没底。
“那两年我没做一点儿科研。”回想起当年的日子,柴立元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他说,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专业建设,就是建实验室,就是搭平台。也是年轻胆大,2001年,当时还只是冶金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的他,在导师、系主任张传福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,居然和同事们攒了个国际学术研讨会——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及其资源化国际会议,“写信封贴邮票”,居然也请来了来自加拿大、日本、韩国、南非、中国香港及内地的100多位专家学者,收到了上百篇论文,其中92篇正式结集出版。
从1999年回国,到2004年国家环保部的工程技术中心落户学校,同时拿到这个专业的博士点,再到2011年拿到科技部的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,获得三个国家科技奖二等奖……如今,学科师资队伍已成为拥有25名教授的40多人的大团队(包括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、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以及首批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),学科排名进入全球ESI前1%,整整20年,可以说,柴立元和同事们创下了奇迹。
治污、治废:“不成功就改行”
学科建设的目的不仅仅是招学生,更不仅仅是发论文,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,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。
有色冶金环境工程,主要的任务是研究如何治理冶炼过程中的废气、废水及固体废物污染。而这“三废”的治理,都必须到生产一线去。“但当时没名气,拿不到什么项目。”团队成员闵小波教授说。
那就自己找。
原长沙铬盐厂倒闭后,有42吨铬渣一直堆放着无法处理。“铬渣中的水溶性六价铬被列为对人体危害最大的8种化学物质之一,是国际公认的3种致癌金属物之一。”柴立元介绍,而且铬渣堆积占用了大量土地,也使土壤和地下水受到了严重污染。如果按传统的“湿法”和“干法”两种办法处理铬渣,需资金2.5亿元,如果要治理已被污染的土地,至少还得10多亿元。当时,全国各地现存的铬渣达600万吨,需要数百亿元的治理费用。因此,铬渣的治理一直困扰和阻碍我国铬化工行业的发展。
柴立元和团队决定,就拿这个硬骨头开刀!
传统的铬渣治理,多是将其高温处理,但如此大规模的堆积成山的铬渣,如何加以高温?显然不现实。柴立元和他的同事们一次次往那个铬渣山里跑,无数次观察“山”里的情况。他们惊奇地发现,“毒山”里居然有植物顽强地生长!大家意识到,这个植物的生长土壤里一定有对付铬渣的独特物质。经过8年艰苦的研究,2005年,柴立元和他的“铬渣生物解毒”课题组,终于从铬渣堆埋场附近的淤泥中分离驯化出某菌株,首创了细菌直接解毒铬渣并选择性浸出回收铬的方法,实现了铬渣及堆场土壤的低成本高效治理。
铬渣的成功治理,让柴立元团队积累了经验,也在业内渐渐有了名气。国有大型企业湖南省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找上门来了,请他们治理含铍废水。我国最大的铅锌联合冶炼企业株冶集团找上门来了,“这桶废水处理不好,株冶厂就没救了”,企业负责人将柴立元团队请到现场,拎来一桶冶炼烟气洗涤废水,对柴立元说。
废水,废水,都是废水!柴立元心情沉重。
此前,处理这些工业废水的方法,多是利用石灰中和沉淀废水中的重金属,但因废水中重金属浓度高、种类杂,石灰很难“抓住”全部重金属离子,处理后的废水不仅难以达到国家最新发布的排放标准,还会产生大量淤泥,且处理后的水基本难以再利用,企业很是头疼。2010年,因生产过程中发生铊泄漏,拥有5000多名员工的韶关某大型企业不得不停产,3万吨废水无法处理!
“真的都是国家重大需求。”采访时,柴立元一一向记者介绍这些项目。耳闻一件件重金属污染事件的发生,看到一家家企业负责人期盼的眼神,柴立元深感自己作为一名科研人员的责任和使命。
“传统办法只能‘抓住’一两种重金属离子,有没有一种东西可同时‘抓住’多种呢?”柴立元团队确立了处理废水的思路:既要去除其中多种有害重金属,又要可回收再利用。得益于处理铬渣的经验,团队发现,微生物对重金属有极大的“抓附”作用,且像有多只“手”一样,可同时“抓住”多种有害重金属。
可是,能处理废水的微生物哪里有呢?不知在阴沟里、淤泥里取样多少回,也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,更不知失败了多少次,终于,柴立元和大家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混合菌群。“目标菌种找到了,再大量培养,做成药剂。”闵小波告诉记者,2005年,实验室制剂完成。这个时候正好株冶找上门来,实验室成果要真刀实枪地投入使用了,大家都很兴奋。
“我记得很清楚,2007年春节假期还没过完,正月初八,柴老师就带领我们进驻株冶。”副教授王庆伟说,他当时还是研究生。
这一待就是大半年。实验室试验的时候,制剂效果非常好,可当大规模使用时——当时株冶一天要排放14000立方米的废水——菌群们就不“听话”了。到底能不能成功?有人甚至有些动摇。“第一炮一定要打响。”柴立元既要当总指挥拿方案,又要做政委给大家打鸡血。他和师生们用彩条布在厂房边搭起了简陋的“实验室”,团队十几个人轮班守现场,日夜调试。“那气味,熏死个人,眼睛睁不开,鼻涕直流,喉咙难受。”柴立元说自己无法形容那刺鼻的臭味,只记得当时一名年轻的女研究生,本来白净的脸上没几天就长满了疙瘩,柴立元自己也免疫力下降,吃了一年半的药才调理好。
“背水一战。”当时大家都铆着一股劲儿,“不成功就改行”,他们甚至不给自己留退路。
终于,他们成功了,这套后来命名为“重金属废水生物制剂法深度处理技术”的方案,让株冶重获生机。如今,这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100多家大中型涉重金属企业的近200项工程,实现年处理重金属废水超过1亿立方米,解决了有色冶炼清洁生产过程终端污染治理环节的重大工程难题,成为行业标杆。2011年,这项技术摘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。
接下来几年,柴立元团队陆续攻克一个又一个“治废”难题。“生物制剂处理含铍废水新技术”“选—冶联合清洁炼锌技术”“含重金属低浓度二氧化硫烟尘净化回收技术”等10多项先进适用工程化技术相继研发成功,基本形成了有色冶炼行业的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体系。“有色冶炼含砷固废治理与清洁利用技术”“冶炼多金属废酸资源化治理关键技术”还分别获得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。
发明不断,获奖多多,可柴立元还是高兴不起来。为什么?因为技术推广太难了。治理重金属污染的生物药剂,企业使用起来是以吨为单位,在生产车间使用时还得有相应的装备系统。还没开始治污,还不知效果如何,就要掏一大笔钱,企业一般都有些犹豫。为解决这个问题,柴立元又领着团队发明了一个类似大集装箱的移动式装备系统,可处理20多种废水、废气、废渣,企业有需要,大货车装上这个“集装箱”就能“开战”。曾经有家企业,任柴立元团队如何反复宣讲技术,就是不信。团队将这个大“集装箱”拖到现场,7天之后,效果出来了,企业心服口服,用上了他们的技术。“等于是企业看到了活生生的可研报告。”闵小波说。
2010年北江铊污染治理、2012年广西龙江镉污染治理、2013年广西贺江铊污染治理……团队都是拉着这个大“集装箱”解危的。“29个省份的200多家大中型企业用上了我们的技术。”柴立元说,每实施一个工程,他就在地图上画一面红旗,“希望插遍全中国。”这是采访时他跟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甘当工作狂:“要抢时间,形势逼人”
2013年11月4日,是柴立元终生难忘的日子,这一天,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南大学调研科技创新,来到了他所在的实验室。总书记对柴立元带领团队刻苦攻关、勇于创新的精神给予高度赞许。“当时我就在心里暗自承诺:请总书记放心,我们一定努力工作,研发出更多、更好的先进技术,为打造青山绿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”柴立元说。
“工作狂。”采访中,几乎所有的同事、学生,都是异口同声地这样评价柴立元。“他有句口头禅,宁可少活10年,也要把这个事做好。”闵小波说,柴老师是不要命地在干活。
团队刚成立时才3个人,柴立元领着大家既要搞学科建设,又要到企业四处找课题,一天24小时连轴转。2001年做郴州治理砷污染项目时,团队又接到水口山一家企业的请求,“又要上课,又要做科研,我们累惨了。”闵小波说,他那时每周有两次课,柴老师和团队成员们在衡阳水口山、郴州项目点轮番跑,“稻草都睡过。”路不好走,闵小波又刚拿驾照,自己开车到这些企业磕磕绊绊要大半天,有时一个星期要跑两三趟,累得话都不想说。
“学到了坚持和拼命两个词。”李青竹是环工系的第二届学生,2001年进校,后硕博连读留校工作,她给记者讲了个细节:2018年,柴立元刚在北京搞完一个答辩,又马上回到长沙搞省里的答辩,在等候答辩的间隙,他靠在椅背上就睡着了。这一幕让李青竹印象深刻,在老师榜样力量的激励下,年轻的李青竹今年破格升为教授。
“等车候机睡着是常事。”闵小波说,他印象最深的是无论坐火车还是飞机,柴立元永远是卡着点走,有次到机场,算好时间应该来得及,但没想到遇上修路临时要改道,闵小波只好“把车开得像飞机一样,飞起”。
但一有工作,他又完全可以不睡。博士生彭宁回忆,2013年某天凌晨3点多钟,他们在郴州一家企业的实验有了大进展。大家第一时间发短信向柴立元报喜,没想到几秒钟后,同学们就收到了老师的回复。博士生石岩,2010年刚来时写了关于微生物治污的一些想法,“学冶金的老师能提多少建议”,他在心里还没嘀咕完,柴立元的意见就来了,“工作狂,我们年轻人都搞不过他”。
团队的杨卫春老师则给记者讲了这样几件小事:有次,柴立元上午到岳阳出差,下午2点就赶到教室给本科生上课,午饭都没吃,而谁都知道,他的胃不好;2018年,柴立元搞一个材料到凌晨2点多钟,发现实验室有个房间灯还亮着,他硬是四处找人,直到把灯关了才离开。2019年国庆节,“七天假只休了一天。柴老师只让我们看完阅兵式,就把团队拉到浏阳道吾山,让我们闭关讨论问题写项目书。”杨卫春“控诉”道。他说,自2009年加入团队以来,几乎从来就没有寒暑假的概念,过年也最多休个五六天。
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“工作狂”模式,大家成长迅速,“感觉越来越有底气了”。刚给株冶治理完废水,企业又提出要求,希望治理废酸。“我国是世界冶炼第一大国,行业废酸排放量每年高达2000万立方米。”柴立元介绍,废酸高效治理与资源化是国际上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而冶金环境工程就是既要绿水青山,又要金山银山。“我们花了十几年,才完成这个项目。”柴立元说。如今,这项技术已在紫金矿业集团、五矿集团、宝武集团等国内十多家大型铜、锌、钢铁冶炼企业工业化应用,与紫金集团海外项目签订合作协议在刚果(金)推广。近三年共处理废酸373万立方米,减排危废物体6.73万吨。来自学校科研处的统计表明,这些年来,柴立元团队发明创新的10多项工程技术,累计至少创造了上百亿元的经济效益,社会与环境效益更是显著。
“要抢时间,形势逼人啊。”记者向柴立元转述同事们的“控诉”,他回答说,团队大,任务重,企业需求多,“不拼不行啊”。“我理解,中南人的精神就是奋斗精神。”他说,这些年,广西龙江镉污染,湖南娄底双峰铬污染,浙江台州铅污染……频频爆发的重金属污染事件,已经严重破坏生态,危害群众健康,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。随着国家出台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,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防治重金属污染,保护绿水青山,已经成为我国重大战略需求。作为党和人民培养的科技工作者,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己任,义不容辞。为了总书记的嘱托,为了一路走来大家的帮助,他必须成为“工作狂”。
采访中,柴立元一再述说着一路走来帮助过他和团队的人们,述说着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,没有国家的培养,当年的农村穷孩子不可能上大学做研究,更不可能成为院士。
他说,自己的梦想是:全国规模以上有色冶金企业1600多家,能建起一个数据库,从技术方面对企业全流程进行监管,从源头上防治污染。“全国都无污染了,我也就瞑目了。”与记者临别时,他说。

